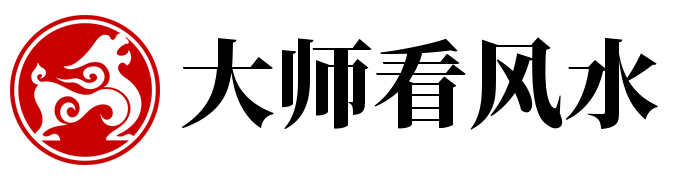红颜薄命潘金莲
欢迎关注并转发
潘金莲
在西门府女子中,潘金莲占据几项之最:最美貌、最具才华、最放荡、出身最差、心气最高。
金莲的美貌毋庸置疑。第九回金莲初入西门府,连月娘也被她的美貌震慑了:“这妇人年纪不上二十五六,生的这样标致。但见:眉似初春柳叶,常含着雨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暗带着风情月意。纤腰袅娜,拘束的燕懒莺慵;檀口轻盈,勾引得峰狂蝶乱。玉貌妖娆花解语,芳容窈窕玉生香……吴月娘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论风流,如水晶盘内走明珠;语态度,似红杏枝头笼晓日。”对金莲俯仰百变的风姿,月娘嘴上不说,心内暗叹:“怪不的俺那强人爱他!”可见,金莲的美不仅征服了男人,还征服了女人。
金莲的美丽还不只在于体态容貌,更在于一言一语的活泼、一举一动的俏丽。她活泼娇俏,仿佛桃花照眼,所过之处,无不留芳。看她第一回对武松殷勤叮嘱:“奴这里等候哩!”一句话里,包含无限的温婉、柔情。与她遭受的冷眼对照,不由令人心生恻隐。在被武松粗鲁伤犯时,她紫涨了面皮,对武大指骂:“你这个混沌东西。有甚言语在别处说,来欺负老娘!我是个不带头巾的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也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不是那腲脓血搠不出来鳖!老娘自从嫁了武大,真个蚂蚁不敢入屋里来,甚么篱笆不牢犬儿钻得入来?你休胡言乱语,一句句都要下落!丢下一块瓦砖儿,一个个也要着地!”言词生动,逻辑清晰,又带着金莲式的脆生生的直爽。武松被骂得高兴,反而向她敬酒。
第二回她跟西门庆谈话,西门庆故意问她夫家,然后“呆了脸,半日不语”,突然失声叫屈。金莲看他演戏,便“一面笑着,又斜瞅了他一眼,低声说道:‘你又没冤枉事,怎的叫屈?’西门庆道:‘我替娘子叫屈哩!’这妇人一面低着头弄裙子儿,又一回咬着衫袖口儿,咬得袖口儿格格驳驳的响,要便斜溜他一眼儿”。其实,西门庆叫屈,无疑打中了金莲。金莲被勾动心事,先是笑,然后弄裙子儿、咬袖口儿、斜溜西门庆,心理的变化清晰可见。“笑”、“弄衣裙”是掩饰窘迫,“咬袖口儿”是恨命运多舛,而“斜溜西门庆”,则是暗暗憧憬了。
第八回,西门庆得手后将她冷落,金莲使王婆去请。西门庆摇着扇儿,带酒半酣进来,金莲与他斗嘴,道:“大官人,贵人稀见面!怎的把奴丢了,一向不来傍个影儿?家中新娘子陪伴,如胶似漆,那里想起奴家来!”绵里藏针,直指西门庆喜新厌旧、另娶玉楼一事。西门庆自然不承认:“你休听人胡说,那讨什么新娘子来!因小女出嫁,忙了几日,不曾得闲工夫来看你。”金莲又逼道:“你还哄我哩!你若不是怜新弃旧,另有别人,你指着旺跳身子说个誓,我方信你。”西门庆久惯牢成,果然就起誓:“我若负了你,生碗来大疔疮,害三五年黄病,匾担大蛆叮口袋。”男人虽无赖,金莲到这田地,也只有这个依傍了,遂见好即收,骂他:“负心的贼!匾担大蛆叮口袋,管你甚事?”话锋陡转,却骂得深情款款、风韵无限。且骂且一手把西门庆帽儿撮下来,向他头上拔下簪儿。见上面鈒的两溜字,知是妇人与的,遂夺了放在袖里,向西门庆发作:“你还不变心哩!奴与你的簪儿那里去了?”西门庆撒个谎,金莲却不好糊弄。她将手向他脸边弹个响榧子,戏道:“哥哥儿,你醉的眼恁花了,哄三岁孩儿也不信!”王婆也一旁帮腔。西门庆无力招架,拿王婆撒气,嗔道:“紧自她麻犯人,你又自作耍。”一语未了,金莲又把他手中一把红骨细洒金、金钉铰川扇儿夺了。迎亮处照见上面许多牙咬的碎眼儿,顿时发作,不由分说,两把就折了。西门庆待救时,已扯得稀烂,只得讪讪道:“这扇子是我一个朋友卜志道送我的,一向藏着不曾用,今日才拿了三日,被你扯烂了。”半是惋惜、半是解释,只对金莲无可奈何。
金莲喜欢与西门庆调笑。第十一回,金莲赌棋输了,“西门庆才数子儿,被妇人把棋子扑撒乱了。一直走到瑞香花下,倚着湖山,推掐花儿。西门庆寻到那里,说道:‘好小油嘴儿!你输了棋子,却躲在这里。’那妇人见西门庆来,昵笑不止,说道:‘怪行货子!孟三儿输了,你不敢禁他,却来缠我!’将手中花撮成瓣儿,洒西门庆一身”。扑棋耍赖、捊花打人,金莲都那样俏丽。同样的场景,还有扑蝶、簪花、梳妆等等。可以说金莲是西门府一道长年不衰,而又四时不同的风景。
使金莲之美更具韵味的,是她的文采。金莲弹唱出身,在戏文熏陶中长大,不仅识文断字,而且具有相当的诗词水平。第八回金莲第一次给西门庆上寿,第一次展露才华:“一边吩咐迎儿,将预先安排下与西门庆上寿的酒肴,整理停当,拿到房中,摆在桌上。妇人向箱中取出与西门庆上寿的物事,用盘盛着,摆在面前,与西门庆观看。却是一双玄色段子鞋;一双挑线香草边阑、松竹梅花岁寒三友酱色段子护膝;一条纱绿潞绸、水光绢里儿紫线带儿,里面装着排草玫瑰花兜肚;一根并头莲瓣簪儿。簪儿上鈒着五言四句诗一首,云:奴有并头莲,赠与君关髻。凡事同头上,切勿轻相弃。西门庆一见满心欢喜……说道:‘怎知你有如此聪慧!’”
第十二回,西门庆流连烟花不归。月娘看他生日将近,使玳安拿马去接。“潘金莲暗暗修了一柬帖,交付玳安,教:‘悄悄递与你爹,说五娘请爹早些家去罢。’”却是一首《落梅风》,倾诉相思之情。金莲以为西门庆喜欢这个,才填词去打动。但帖子尚未交付西门庆,便被桂姐儿一手抓去,叫人念给她听。听毕,就走入房中,使起性来。西门庆见他心爱的粉头着恼,连忙把帖子扯得稀烂。从此以后,金莲便不再在西门庆跟前舞文弄墨。
比起武夫,金莲更认可文人。第十九回,西门庆整治蒋太医蒋竹山,“乘着欢喜,向妇人(金莲)道:‘我有一件事告诉你,到明日,教你笑一声。你道蒋太医开了生药铺,到明日管情教他脸上开果子铺来。’妇人便问怎么缘故。西门庆悉把今日门外撞遇鲁、张二人之事,告诉了一遍。妇人笑道:‘你这个众生,到明日不知作多少罪业。’又问:‘这蒋太医,不是常来咱家看病的么?我见他且是谦恭,见了人把头只低着,可怜见儿的,你这等做作他!’西门庆道:‘你看不出他。你说他低着头儿,他专一看你的脚哩。’妇人道:‘汗邪的油嘴!他可可看人家老婆的脚?我不信,他一个文墨人儿,也干这个营生?’”无论说竹山是“文墨人儿”,还是说他对人“谦恭”,金莲都明显偏向蒋竹山,流露出对他的怜惜。
西门庆不能赏识金莲的风雅,东京来的女婿陈敬济,却能与她唱和,这一点无疑推动了两人的私情。第八十二回西门庆死后,金莲为告诉陈敬济在荼縻架下约会,拿一个纱香袋装一缕头发,并些松柏儿,用自己袖的银丝汗巾儿裹了,填了首《寄生草》,一并寄与敬济。词曰:“将奴这银丝帕,并香囊寄与他。当初结下青丝发,松柏儿要你常牵挂,泪珠儿滴写相思话。夜深灯照的奴影儿孤,休负了夜深潜等荼縻架。”敬济便回她一柄湘妃竹金扇儿、一首《水仙子》,词曰:“紫竹白纱甚逍遥,绿囗青蒲巧制成,金铰银钱十分妙。美人儿堪用着,遮炎天少把风招。有人处常常袖着,无人处慢慢轻摇,休教那俗人见偷了。”意思则是叫金莲小心。此外,二人闹矛盾的时候,也常常会以诗词表达情绪。金莲去寻敬济,敬济酒醉不醒。金莲摸到他袖中一根玉楼的簪儿,疑心他与玉楼有首尾,有意慢慢审他,遂在墙上题诗。诗曰:“独步书斋睡未醒,空劳神女下巫云。襄王自是无情绪,辜负朝朝暮暮情。”之后悻悻而去。直到最后,敬济约金莲私奔,仍然是用诗词的形式表达的。第八十五回,敬济封了个柬帖,写着一首《红绣鞋》:“袄庙火烧皮肉,蓝桥水淹过咽喉,紧按纳风声满南州。洗净了终是染污,成就了倒是风流,不怎么也是有。”托薛嫂交给金莲。意思就是暗示私奔了。金莲觉得时机不成熟,便未答应,但还是回了他一方白绫帕,而帕上也题了首相思词。总之,敬济与金莲这段恋情始终伴随着诗词唱和。不管这些诗词作得如何,起码二人都有这雅兴,所以从有些方面看,敬济似乎更适合金莲。
除了诗词,金莲在戏曲上也颇有造诣。第七十三回,西门庆因怀念瓶儿,令小优儿唱“忆吹箫,玉人何处”,金莲便吃醋了,与他吵闹后回到上房。大妗子不解其故,月娘向她解释了,杨姑娘便夸金莲聪明。月娘道:“他什么曲儿不知道!但题起头儿,就知尾儿。象我每叫唱老婆和小优儿来,只晓的唱出来就罢了。偏他又说那一段儿唱的不是了,那一句儿唱的差了,又那一节儿稍了。但是他爹说出个曲儿来,就和他白搽白乱,必须搽恼了才罢。”虽然透着不满,但显然也认可金莲这种才能。金莲常常利用自己的这项才能作为武器。第二十一回,金莲叫春梅等四个家乐,唱了一套《南石榴花》“佳期重会”,目的是讥讽月娘烧夜香。第二十回,在瓶儿的会亲宴上,金莲当众指出小妾不当唱“喜得功名遂”、“天之配合一对儿,如鸾似凤”、“永团圆,世世夫妻”等曲,以表达自己的不满。
金莲不仅常以曲文为话头,常常也自弹自唱、抒发情怀。第一回,金莲被嫁给武大,抑郁不乐,“常无人处,唱个《山坡羊》为证:想当初,姻缘错配,奴把你当男儿汉看觑。不是奴自己夸奖,他乌鸦怎配鸾凤对!奴真金子埋在土里,他是块高号铜,怎与俺金色比!他本是块顽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体!好似粪土上长出灵芝。奈何,随他怎样,到底奴心不美。听知:奴是块金砖,怎比泥土基!”第八回,金莲嫁入西门府前,思念西门庆,也“独自弹着琵琶,唱一个《棉搭絮》”:“谁想你另有了裙钗,气的奴似醉如痴,斜倚定帏屏故意儿猜,不明白。怎生丢开?传书寄柬,你又不来。你若负了奴的恩情,人不为仇天降灾。”第三十八回,西门庆冷落她,金莲独守空房,雪夜遣怀,自弹自唱《二犯江水儿》。听春梅说西门庆在隔壁,骂几句负心贼,由不得眼中扑簌簌落泪,渐渐高声弹唱道:“心痒痛难搔,愁怀闷自焦。让了甜桃,去寻酸枣。奴将你这定盘星儿错认了。想起来,心儿里焦,误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稍来没下稍。”最后西门庆听见,才来伴了一宿。不过,这样的情形,全书仅此一次。从此以后,金莲被冷落渐渐成为定局。从瓶儿母子去世,到西门庆暴毙,金莲每况愈下,再不歌唱。
除此之外,令金莲艳光夺人的,还有她的口才。金莲的口才,西门府无人能敌,玉楼也逊她一筹。
且看第十一回金莲与雪娥交锋。雪娥挨打之后,便去告状。金莲已提防到这个,先去窗下潜听。听见雪娥说她浪,又说她以前在武家毒杀亲夫之事——这项罪名很大,也的确说中金莲要害。金莲不能容忍,便走出来与雪娥对骂。她抓住雪娥话里的漏洞做文章,“望着雪娥说道”:“比如我当初摆死亲夫,你就不消叫汉子娶我来家,省得我霸拦着他,撑了你的窝儿。论起春梅,又不是我的丫头,你气不愤,还教他伏侍大娘就是了。省得你和他合气,把我扯在里头。那个好意死了汉子嫁人?如今也不难的勾当,等他来家,与我一纸休书,我去就是了。”一番话,只管抬出西门庆和月娘来替自己正名,不仅问住了雪娥,也顺带堵了许多说是道非的嘴。笨拙的雪娥无言以对,只得怪金莲口才太好,对月娘道:“娘,你看他嘴似淮洪也一般,随问谁也辩他不过。”
金莲自然比雪娥优秀。就连西门庆的亲随、西门府第一乖觉油滑的玳安,也被金莲收拾得服服帖帖。第二十一回,月娘烧夜香,与西门庆私下和解后,玉楼主持众妾凑钱请酒道贺,叫了玳安来置办。金莲便问西门庆昨夜之事,玳安说了一遍,道:“爹使性骑马回家,在路上发狠,到明日还要摆布淫妇哩。”金莲先感叹一句:“贼淫妇!我只道蜜罐儿长年拿的牢牢的,如何今日也打了?”随即向玳安发难:“贼囚根子,他不揪不采,也是你爹的婊子,许你骂他?想着迎头儿我们使着你,只推不得闲,‘爹使我往桂姨家送银子去哩!’叫的桂姨那甜!如今他败落了来,你主子恼了,连你也叫他淫妇来了!看我明日对你爹说不说。”玳安冷不丁被擒住要害,动弹不得,只道:“早知五娘麻犯小的,小的也不对五娘说。”玉楼与金莲都趁机说:“小囚儿,你别要说嘴。这里三两一钱银子,你快和来兴儿替我买东西去。今日俺们请你爹和大娘赏雪。你将就少落我们些儿,我教你五娘不告你爹说罢。”这样一来,玳安自然乖乖的,不敢弄半点虚假了。
乖滑的玳安还被金莲拿捏,锯嘴葫芦瓶儿就更无奈了。第五十回,由于西门庆常在瓶儿房中,冷落其他人,金莲便向月娘说瓶儿是非。西门大姐告诉了瓶儿,结果,“这李瓶儿不听便罢,听了此言,手中拿着那针儿通拿不起来,两只胳膊都软了,半日说不出话来,对着大姐掉眼泪,说道:‘大姑娘,我那里有一字儿?昨晚我在后边,听见小厮说他爹往我这边来了,我就来到前边,催他往后边去了。再谁说一句话儿来?你娘恁觑我一场,莫不我恁不识好歹,敢说这个话?设使我就说,对着谁说来?也有个下落。’大姐道:‘他听见俺娘说不拘几时要对这话,他也就慌了。要是我,你两个当面锣对面鼓的对不是!’李瓶儿道:‘我对的过他那嘴头子?只凭天罢了。他左右昼夜算计的只是俺娘儿两个,到明日终久吃他算计了一个去,才是了当。’说毕哭了”。
瓶儿面对金莲的中伤,表现得十分软弱,这是由于她在“口若淮洪”的金莲跟前,极度缺乏自信的缘故。金莲的口才好得令人害怕,而且又口无遮拦,什么都敢说。她说话直率、大胆的程度,往往令人咋舌。这是她与玉楼、月娘的最大差别。西门庆就常被金莲的直率,“擦刮得眼直”。
第十三回,西门庆与瓶儿私通,众人都不言语。金莲发现了,“一手撮着西门庆耳朵,骂道:‘好负心的贼!你昨日端的那里去来?把老娘气了一夜!你原来干的那茧儿,我已是晓得不耐烦了!趁早实说,从前已往,与隔壁花家那淫妇偷了几遭?一一说出来,我便罢休。但瞒着一字儿,到明日你前脚儿过去,后脚我就吆喝起来,教你负心的囚根子死无葬身之地!你安下人标住他汉子在院里过夜,却这里要他老婆。我教你吃不了包着走!嗔道昨日大白日里,我和孟三姐在花园里做生活,只见她家那大丫头在墙那边探头舒脑的,原来是那淫妇使的勾使鬼来勾你来了。你还哄我老娘!前日她家那忘八,半夜叫了你往院里去,原来她家就是院里!’”泼辣厉害的金莲,一通大骂,句句都直指西门庆的虚伪、丑恶,顿时唬得西门庆装矮子,跌脚跪在地下,笑嘻嘻地求饶。对于西门庆陷害无辜的蒋太医,也只有金莲敢骂西门庆:“你这个众生,到明日不知作多少罪业。”“这蒋太医,不是常来咱家看病的么?我见他且是谦恭,见了人把头只低着,可怜见儿的,你这等做作他!”西门庆娶瓶儿后,次日,金莲便特地早早起来,拦住西门庆就是一顿讥嘲:“昨日那等雷声大雨点小,要打着教她上吊。今日拿出一顶鬉髻来,使的你狗油嘴鬼推磨,不怕你不走。”如此直率,毫不避讳,完全是她一贯的作风。西门庆拿她无法,只好笑:“这小淫妇儿,单只管胡说!”
金莲的这种泼辣性格,有时候是“爱出尖儿”、“咬群儿”,过于牙尖嘴利;有时候这种性格又表现为率真、不做作,在西门府众多城府甚深的女人中显得十分可贵、可爱。
由于这种性格,金莲才会嘲笑月娘烧夜香的做作与虚伪。也因为这种性格,只要事情里面有诈,或者表里不一,金莲都会立刻直言不讳地揭穿。金莲如此,其中有她的嫉妒心作祟——对于这一点,她其实毫不掩饰——同时也反映了她求真求实的执着和勇气。
例如,第四十一回官哥儿与长姐儿结亲,因长姐儿是庶出,西门庆心疼孩儿,再三说:“既做亲也罢了,只是有些不搬陪。乔家虽有这个家事,他只是个县中大户白衣人。你我如今见居着这官,又在衙门中管着事,到明日会亲酒席间,他戴着小帽,与俺这官户怎生相处?甚不雅相。就是前日,荆南冈央及营里张亲家,再三赶着和我做亲,说他家小姐今才五个月儿,也和咱家孩子同岁。我嫌她没娘母子,是房里生的,所以没曾应承他。不想到与他家做了亲。”显然,西门庆根本不把官哥儿当庶出。但是,官哥儿本来就是庶出。月娘老辣,便不言语,心直口快的金莲却先接过来道:“嫌人家是房里养的,谁家是房外养的?就是乔家这孩子,也是房里生的。正是险道神撞着寿星老儿——你也休说我长,我也休嫌你短。”一句直指事实,正中西门庆要害。西门庆听了不由大怒,骂道:“贼淫妇,还不过去!人这里说话,也插嘴插舌的。有你甚么说处!”
又如,第七十三回,玉楼生日,西门庆吩咐小优儿从“忆吹箫,玉人何处也”、“他为我褪湘裙杜鹃花上血”,直唱到“一个相府内怀春女,忽剌八抛去也。我怎肯恁随邪,又去把墙花乱折!”众人不知觉,独金莲知道西门庆意思,便认真要和西门庆理论。西门庆与月娘等人在房中闲谈,金莲便蹑足进去,立在炕儿背后,忽然开口讥道:“哥儿,你脓着些儿罢了。你那小见识儿,只说人不知道。他是甚‘相府中怀春女’?他和我都是一般的后婚老婆。什么他为你‘褪湘裙杜鹃花上血’,三个官唱两个喏,谁见来孙小官儿问朱吉,别的都罢了,这个我不敢许。可是你对人说的,自从他死了,好应心的菜儿也没一碟子儿。没了王屠,连毛吃猪!你日逐只噌屎哩?俺们便不是上数的,可不着你那心罢了。一个大姐姐这般当家立纪,也扶持不过你来,可可儿只是他好。他死,你怎的不拉住他?当初没他来时,你怎的过来?如今就是诸般儿称不上你的心了。题起他来,就疼的你这心里格地地的!拿别人当他,借汁儿下面,也喜欢的你要不的。只他那屋里水好吃么?”说得西门庆无可奈何,只是笑,又骂她:“怪小淫妇儿,胡说了你,我在那里说这个话来?”金莲便将时间、地点一一指出,又拿出西门庆与如意儿之事,指责他言行不一。金莲说:“就是当初有他(瓶儿)在,也不怎么的。到明日再扶一个起来,和他做对儿就是了。贼没廉耻撒根基的货!”骂得西门庆急了,跳起来,赶着拿靴脚踢她。金莲便夺门跑了。
这样一个富有才华、又颇具个性的美女金莲,却出身贫寒、经历坎坷。她是南门外潘裁缝的女儿,得名于一双小脚。九岁时死了父亲,母亲潘姥姥“度日不过,从九岁卖在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闲常又教他读书写字”。所以,金莲实际上是由王招宣府教养,在诗词戏曲的熏陶中长大的。正是这样的环境,塑造了金莲的性格。无论是她的才华,还是她的个性,都与这段成长经历不无关系。
从《金瓶梅》中的韩道国家的爱姐儿、贲四家的长儿的经历来看,金莲进王招宣府、张大户家,是当时贫家女子的普通出路。她们这类女子,因贫穷不能婚嫁,只能卖身进入富室,来谋条出路。她们做奴仆几年,或配了小厮,如蕙莲、一丈青;或被主人收用,如雪娥、春梅。所以,金莲被张大户收用,也十分自然。这件事是金莲命运的必然,但也是她悲剧的开端:正因为落入张大户之手,金莲才会被许配武大;正因为许配了武大,才有了她与武松、与西门庆的纠葛,有了她在西门府的一切故事。金莲似乎注定有一个拿不出手的母亲、有在王招宣府难于启齿的成长经历,似乎注定会与武松这样的姻缘错过,似乎注定要带着轻浮放浪的名声、通奸杀夫的罪过以及弹唱姐儿的卑微和缺陷进入西门府。
在西门大官人与月娘管理下的西门府,其实很讲究门第。孟玉楼死了丈夫,以杨家大娘子的身份,明媒正娶改嫁过来,还不时被月娘讥嘲,金莲承受的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在金莲背负的所有压力当中,杀夫是最大的十字架。《金瓶梅》中的武大,的确相当不堪。毒杀武大一事,其实是王婆、西门庆主谋。然而,男权社会习惯于将所有罪恶都推给女人。小说并未正面提及金莲初进西门府时因这件事而面对的流言蜚语,但雪娥的一番话,却暗中点明了西门府众人对这件事的普遍看法。缺心眼的雪娥骂金莲:“背地干的那茧儿,人干不出,她干出来。当初在家,把亲汉子用毒药摆死了。”认为这件事金莲应负全部责任,这种观点确实可能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这个罪名的沉重压力下,金莲在西门府变得特别多疑,喜欢听篱察壁、颠寒作热。正是由于这种重压,金莲不仅挑唆西门庆打了多嘴的雪娥,后来更弄得来旺家破人亡。从进入张大户家开始,金莲的人生便仿佛中了魔咒,罪恶连连,不能自拔。
金莲之所以会在精神重压下不断作恶而不能醒悟,也是因为她性情简单,故而经常被人利用。玉楼说她是个“有口无心的大行货子”,简直比金莲自己还了解她。金莲虽有才华,其实也跟雪娥一样,都是喜怒形于色、言行举止全凭本能的女子。比起雪娥,金莲唯一的幸运是拥有西门庆对她的宠爱。实际上,看起来聪明伶俐的她,有时候跟雪娥一样糊涂,意识不到危险,不善于保护自己。她被月娘和玉楼利用,逼死了蕙莲儿,一直怀有沉重的负罪感。直到多年以后,她才稍稍明白此事背后有些蹊跷,向玉楼埋怨:“大姐姐也有些不是……”至此还完全不知道玉楼在其中的“贡献”。金莲被人利用,绝不止这一回,第五十九回的官哥儿之死也是一例。
表面上看,官哥儿是被金莲的猫唬死的。金莲的猫叫雪狮子,金莲十分喜爱。西门庆不在房中时,金莲抱着它睡。平时不喂它牛肝、干鱼,只拿红绢裹生肉,令它扑而抓食。其实,这完全是深闺妇人百无聊赖、消遣解闷的行为。但是,由于雪狮子扑了官哥儿,金莲此举便被后人解读为“行此阴谋之事,驯养此猫,必欲唬死其子,使李瓶儿宠衰,教西门庆复亲于己。就如昔日屠岸贾养神獒害赵盾丞相一般”。其实,这种解读多少有些简单,值得商榷。《金瓶梅》作于明朝,在此前后,广为流传的戏曲《赵氏孤儿》、明朝宫廷频出的疑案,构成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由于这种文化背景的影响,后人在解读《金瓶梅》时,便不免先入为主,从而误会作者的本意。其实,说金莲训猫杀子,破绽百出,突兀矛盾,很难自圆其说。
首先,除了金莲的雪狮子,西门府还很有几只猫,对这些猫,瓶儿一向不以为意。有一只玳瑁猫儿。第三十四回,书童为王六儿之事寻瓶儿,见她正在描金炕床上,引着这只猫和官哥儿玩。瓶儿如此,可见养猫并不危险。此外,西门府还有一只黑猫,第五十二回在芭蕉丛下,也把官哥儿唬了。从这件事看,雪狮子唬了官哥儿,其实正如黑猫唬了他一样偶然。第五十九回,雪狮子唬了官哥儿后,月娘便问这猫怎么会来瓶儿房里,迎春回答:“每常也来这边屋里走跳。”可见的确是一般情形。金莲的自我辩解其实也很有力:“早时你说,每常怎的不挝他?可可今日儿就挝起来?”种种迹象表明,猫扑孩子,看来确实是个偶发事件。
其次,金莲是个心直口快、喜怒形于色、没什么心机的人物形象。她嫉妒瓶儿从不掩饰,一贯是当面嘲骂,不给好脸色,要不就去找西门庆告状,通观全书,也没见她像月娘那样背后玩弄心术。在这个事件中,她的猫扑了官哥儿,众人都怨她,她辩解两句无效,便“使性子抽身往房里去了”。从这个动作描写来看,金莲显然是觉得委屈了,并且立刻表现出来。如果她一直处心积虑要设计官哥儿,这时显然应该有更平静、更有效的应对方式,而绝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使性子。
再者,很重要的一点是,就算金莲要设计用猫害官哥儿,也不会蠢到用自己的猫。用自己的猫,相当于杀了人又投案自首。如此浅显的道理,恐怕连雪娥也不会傻到不懂,更何况金莲?
其实,前面已经分析过,官哥儿是被月娘治死的。而月娘之所以敢在此时下手,也是机缘凑巧,恰好有雪狮子和金莲在前面掩人耳目。对于瓶儿母子的受宠,金莲这个“有口无心的大行货子”一直在当众发泄她的嫉妒和不满,因此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她仇视瓶儿母子的既定形象。加上她有毒杀武大、逼死蕙莲的前科,所以雪狮子之事一出,她的凶手之名自然是铁证如山、雷打不动,神仙也救不了了!
金莲稀里糊涂背上人命,甚至连自己也深信不疑。她与如意儿争吵,如意儿只回了一句“正经有孩子还死了哩,俺每到的那些儿!”就气得她大发雷霆。可见,她的确将瓶儿母子之死的责任认在自己身上,如意儿一提此事,便对她刺激很大。
金莲与韩家爱姐儿、贲家长儿都是贫家女儿,走了相似的道路,但与这两人不同的是,金莲与母亲的关系很不融洽。这种不融洽主要是金莲的责任。金莲不愿意接受惨淡的现实,包括她的母亲潘姥姥。从王招宣府,到张大户家,再到武家,再到西门府,金莲其实一直衣食无忧,因而并不能深刻理解生活的艰辛。所以,比起爱姐儿和长儿,金莲的价值观更具有理想色彩。这样的金莲,与独自在外艰难度日的母亲,自然格格不入。潘姥姥经济拮据,金莲嫁了西门庆,母亲自然便指望她接济。金莲在受西门庆宠爱时,这倒不在话下;可被西门庆冷落后,金莲又因极度自尊不愿向月娘屈服,处境日益艰难,便没有能力再接济母亲了。潘姥姥不理解这些,还只当金莲吝啬,母女遂起了龃龉。第三十三回,月娘生辰,因西门庆要和金莲歇,潘姥姥便去瓶儿房中。瓶儿到次日,与了潘姥姥一件葱白绫袄儿、两双缎子鞋面、二百文钱。这些东西对瓶儿来说不算什么,却把潘姥姥喜欢得眉开眼笑。金莲颇看不惯母亲这样,责备她:“好恁小眼薄皮的,什么好的,拿了她的来!”母亲也对女儿不满,讥道:“好姐姐,人倒可怜见与我,你却说这个话。你肯与我一件儿穿?”对于母亲的指责,金莲答道:“我比不得她有钱的姐姐。我穿的还没有哩,拿什么与你!你平白吃了人家的来,等住回可整理几碟子来,筛上壶酒,拿过去还了她就是了。到明日少不的教人惦言试语,我是听不上。”
这一次倒罢了。后来金莲处境不佳,不能调整心态,却对自己的母亲言语过激,甚至辱骂起来。第五十八回西门庆生辰,潘姥姥过来。因当晚西门庆在瓶儿房中歇,金莲嫉妒生气,大醉,打狗打秋菊,对隔壁瓶儿指桑骂槐。瓶儿怕唬着孩儿,再三使人请金莲息怒,金莲不依。潘姥姥看不过,便向前夺女儿鞭子,劝道:“姐姐少打他两下儿罢,惹得他那边姐姐说,只怕唬了哥哥。为驴扭棍不打紧,倒没的伤了紫荆树。”结果,“金莲紧自心里恼,又听见他娘说了这一句,越发心中撺上把火一般。须臾,紫漒了面皮,把手只一推,险不曾推了一交。骂道:‘怪老货,你与我过一边坐着去!不干你事,来劝甚么?甚么紫荆树、驴扭棍,单管外合里应。’潘姥姥道:‘贼作死的短寿命,我怎的外合里应?我来你家讨冷饭吃,教你恁顿摔我?’金莲道:‘你明日夹着那老[毛必]走,怕他家拿长锅煮吃了我!’潘姥姥听见女儿这等擦他,走到里边屋里呜呜咽咽哭去了”。金莲如此过火,实在不堪。而这对母女的冲突,与其说是不伦荒诞,不如说是凄惶可怜。一方面,潘姥姥十分拮据,连轿子钱也出不起;另一方面,金莲虽管着家,但以她的心性,加上月娘敌意的旁观,其实也没什么节余。
从内心真实想法来看,金莲其实是了解并且也愿意帮助自己母亲的,只是力不从心。第七十八回,金莲担心母亲没轿子钱,老早就在门前看挂灯笼等候了。结果母女俩却错过了,倒被月娘有意无意撞见。月娘差小玉来对金莲说:“俺娘请五娘,潘姥姥来了,要轿子钱哩。”月娘如此,无非是打金莲脸,将她一军,要她好看。金莲开始还不信,道:“我在这里站着,他从多咱进去了?”后来知道确是事实,不愿在月娘面前丢人,只得硬着头皮说:“我那得银子?来人家来,怎不带轿子钱儿走!”一面走到后边,见了他娘,也不与轿子钱,只说没有。月娘道:“你与姥姥一钱银子,写帐就是了。”月娘开恩,金莲却不愿领情,硬撑道:“我是不惹他,他的银子都有数儿,只教我买东西,没教我打发轿子钱。”坐了一回,大眼看小眼,外边抬轿的催着要去。玉楼见不是事,向袖中拿出一钱银子来,打发抬轿的去了。
潘姥姥令好强的金莲这般出丑,进房便被尽力数落:“你没轿子钱,谁教你来?恁出丑划划的,教人家小看!”潘姥姥便向女儿告穷:“姐姐,你没与我个钱儿,老身那讨个钱儿来?好容易筹办了这分礼儿来。”金莲道:“指望问我要钱,我那里讨个钱儿与你?你看七个窟窿到有八个眼儿等着在这里。今后你看有轿子钱便来他家来,没轿子钱别要来。料他家也没少你这个穷亲戚!休要做打踊的献世包!‘关王卖豆腐——人硬货不硬。’我又听不上人家那等毩声颡气。前日为你去了,和人家大嚷大闹的,你知道也怎的?驴粪球儿面前光,却不知里面受凄惶。”这对贫穷的母女,各有各的苦楚。
说到“里面受凄惶”,金莲哭了,母亲潘姥姥却并不一定能懂。她也被女儿说哭,不由向人对比瓶儿与金莲:“你娘好人,有仁义的姐姐,热心肠儿。我但来这里,没曾把我老娘当外人看承,一到就是热茶热水与我吃,还只恨我不吃。晚间和我坐着说话儿,我临家去,好歹包些甚么儿与我拿了去,再不曾空了我。不瞒你姐姐每说,我身上穿的这披袄儿,还是你娘与我的。正经我那冤家,半分折针儿也迸不出来与我。我老身不打诳语,阿弥陀佛,水米不打牙。他若肯与我一个钱儿,我滴了眼睛在地。你娘与了我些甚么儿,他还说我小眼薄皮,爱人家的东西。想今日为轿子钱,你大包家拿着银子,就替老身出几分便怎的?咬定牙儿只说没有,到教后边西房里姐姐,拿出一钱银子来,打发抬轿的去了。归到屋里,还数落了我一顿,到明日有轿子钱,便教我来,没轿子钱,休叫我上门走。我这去了不来了。来到这里没的受他的气。随他去,有天下人心狠,不似俺这短寿命。姐姐你每听着我说,老身若死了,他到明日不听人说,还不知怎么收成结果哩!想着你从七岁没了老子,我怎的守你到如今,从小儿交你做针指,往余秀才家上女学去,替你怎么缠手缠脚儿的,你天生就是这等聪明伶俐,到得这步田地?他把娘喝过来断过去,不看一眼儿。”说来说去,只是瓶儿好、金莲恶,却不想自己的女儿,如何有瓶儿优越?母女隔阂到如此地步,真是处在两个世界!
倒是春梅劝姥姥,替金莲鸣不平:“姥姥,罢么,你老人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俺娘是争强不伏弱的性儿。比不的六娘,银钱自有,她本等手里没钱,你只说她不与你。别人不知道,我知道。想俺爹虽是有的银子放在屋里,俺娘正眼儿也不看他的。若遇着买花儿东西,明公正义问他要。不恁瞒瞒藏藏的,教人看小了她,怎么张着嘴儿说人!她本没钱,姥姥怪她,就亏了她了。莫不我护她?也要个公道。”一席话,把金莲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她的要强、坦荡、自尊,在这里十分突出。
潘氏母女的冲突,表面看是为了一点小利,其实是思想和价值观的冲突。直到潘姥姥去世,她也没能与女儿达成谅解与共识。这是金莲的一大悲哀。潘姥姥死后,因月娘不许金莲去发送,金莲便教敬济替她去埋葬母亲。次日敬济走来回话,说葬在门外昭化寺。金莲听她娘入土,不由落下泪来。
金莲的另一大悲哀是武松。作为青年女子,金莲对正常的家庭生活有她的向往——一个健康的丈夫,几个结实的孩子,婚姻恩爱美满。这是金莲的终极追求。小说中许多事情都能体现这一点。比如第二回她打趣王婆:“干娘来得正好,请陪俺娘且吃个进门盏儿,到明日养个好娃娃!”第八十五回,她又劝薛婆子:“到明日养个好娃娃。”指山说磨,其实说出来的是她自己的心声。
俗话说得好:“买金的撞不着卖金。”怀着美好愿望的金莲,却永远与美好的现实无缘。先是被张大户侵占,接着又配给武大,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何等巨大!这时,金莲遇上了武松。只要稍明事理就能看出,武松明显比武大更符合女人的婚恋要求。所以,金莲爱上武松,其实并不是她淫荡,而是如春华秋实、风雨雷电般自然的行为。
但是,金莲与武松注定没有希望。戏曲教给金莲才情,教给她思想,也教给她不合规范的放浪,却没教她如何与现实协调并保护自己。那时文化市场自生自灭,没有组织对其进行甄别、管理,因此鱼龙混杂。少女金莲受这种环境浸润,又没有长者指导(潘姥姥不在,王招宣府女主人林太太品行又很成问题),自然而然习得了当时娱乐界惯有的放荡作风。因此,面对武松,她只可能按照戏文唱的男欢女爱、打情骂俏、私会通奸去表示。而武松生长在正常环境,虽然读书不多,却接受的是传统教育,自然不能接受这样的行为。而且,武松明显是个尚武之人,对戏曲兴趣不大,因此对金莲的举动丝毫不能理解。总之,金莲的放浪与武松的刚正,注定水火冲突。虽然武松也被她的妖娆、炽热多情逼得时时低头,但金莲是他嫂子,武松这位英雄一辈子只认这个。第一回,金莲独自冷冷清清立在帘儿下,看武松踏着乱琼碎玉回来,忙推起帘子,迎笑道:“叔叔寒冷?”武松道:“感谢嫂嫂挂心。”便把毡笠儿除将下来。金莲将手去接,被武松婉拒。武松这样冷淡,金莲也该有所领会了。但金莲欲罢不能。她请武松向火,又搬出些煮熟菜蔬摆在桌子上,要和武松吃酒。武松不知金莲心思,只当寻常吃酒。金莲对他步步紧逼,先道:“叔叔满饮此杯。”武松接过去饮了。金莲一语双关,又要他饮过成双的盏儿,武松也饮了。金莲看这愣头青不醒悟,又换个策略。她“一径将酥胸微露,云鬟半軃,脸上堆下笑来……一只手拿着注子,一只手便去武松肩上只一捏,说道:‘叔叔只穿这些衣裳,不寒冷么?’……武松匹手夺过来,泼在地下说道:‘嫂嫂不要恁的不识羞耻!’又把手只一推,争些儿推金莲一交。又睁眼对金莲说道:‘武二是个顶天立地噙齿戴发的男子汉,不是那等败坏风俗伤人伦的猪狗!嫂嫂休要这般不识羞耻,为此等的勾当,倘有风吹草动,我武二眼里认的是嫂嫂,拳头却不认的是嫂嫂!’”这就是武松对金莲满腔热情的回应。如此粗暴的言词和行为,哪个女子经受得了?何况是娇滴滴的文艺女青年潘金莲。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情窦初开,不想就遭雨横风狂。打虎武松的确是个英雄人物,正义凛然,令人敬佩,只可惜终究少了些人情味。这还不算,愣头青武松走时,郑重其事地告诫金莲,要她“篱牢犬不入”——只差直接叫她别偷人了!
武松的决绝与粗鲁,深深地伤害了金莲,正因如此,西门庆才能乘虚而入。第二回,金莲初见西门庆,一开始对他印象其实并不好:“妇人(金莲)便慌忙陪笑,把眼看那人,也有二十五六年纪,生得十分浮浪。”“浮浪”是金莲对西门庆的第一印象,并不算什么好的,也许在金莲眼中,根本比不上顶天立地的好汉武松。但是,“浮浪”的西门庆有一样胜过武松,就是他爱金莲,又解风情。西门庆的殷勤、温柔,渐渐令金莲心生好感。临别时,“妇人见了那人生的风流浮浪,语言甜净,更加几分留恋”——虽然还是“浮浪”,但之前已加了“风流”。此外,金莲很留恋他的“语言甜净”。不用说,西门庆的温言软语,正是受伤的金莲的对症良药。实际上,从武大到武松,再从武松到西门庆,这只是一个青年女子再正常不过的心路历程,虽然幼稚、迷茫,但绝非淫荡。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西门庆与金莲的情爱进程,便如同搬演戏文。西门庆从相思到求助王婆,再到第三者插足成功,追求金莲的方式是相当文艺的,带着戏曲式的风流。这种方式其实有相当高的风险,以他的势力,完全可以不这样多此一举。如果他跟张大户一样,采用最简单的方式,给武大一些小恩惠,然后直接登堂入室,则完全没有风险。但果真如此,金莲恐怕就要沦为暗娼。此外,金莲嫁入西门府之后,西门庆其实一直对她宠爱有加。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西门庆待金莲其实很真诚、很不错。在这种情况下,金莲的境遇却每况愈下,最后走向了毁灭,这只能是金莲自身的原因了。金莲心高气傲,不能接受现实。戏曲塑造了她,也毁了她。终其一生,金莲都在为消除理想与现实的反差而抗争。她一直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如果金莲现实些,以她的伶俐,命运不会比玉楼逊色,起码也不会落到被人利用、被人整治的地步。其实,月娘当初填房嫁给西门庆,处境并不比金莲好多少。但与金莲不同的是,月娘敢于直面现实,她初来时的低调、对西门庆的顺从等,都是承认现实的结果。当瓶儿的会亲酒令她难受时,她也只是默默退到房中,直到见到哥哥进来,才哭着抱怨了一回。但仅此而已,通篇再没见月娘抱怨第二回。
金莲显然做不到这一点。当年在青石巷武家,金莲就经常吟唱《山坡羊》,把自己比作“凤凰”、“真金”、“灵芝”,可见她自视甚高,因此最后为了摆脱惨淡的现实,才会铤而走险,毒杀亲夫。在西门府,金莲更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她对西门庆,一直是按“凡事同头上”来要求的。然而,这是正妻才有的权利。金莲如此,自然侵犯了月娘的利益。
对金莲的忤逆,月娘不可能无动于衷。不管是对金莲、对瓶儿,还是对其他觊觎大娘子之位的小妾,月娘都会坚决还击,这是她自卫的基本要求。西门府众妾中,雪娥卑微、娇儿安分、玉楼善于掩藏,只有金莲、瓶儿暴露在外。瓶儿或许并无此意,但她拥有的财富、美貌和官哥儿,使月娘不可能忽视她。金莲或许也无此意,但她心高气傲,无视月娘的权威,也使月娘十分猜忌。总之,对这两人,月娘必欲除之而后快。同时,月娘第一能忍耐,骄横如西门庆她都能忍,瓶儿与金莲就更不在话下。忍了几年,终于等到时机,金莲、瓶儿便被她一石二鸟,都摆布了。而这两只呆鸟,至死都没曾怀疑月娘。
月娘在暗中有意无意转嫁给金莲的罪名,使金莲背负的压力日益增加。加上瓶儿母子分宠,金莲在物质与精神上都日益窘迫。这样的现实,自比凤凰的金莲不能接受,却不得不接受。就这样,一开始春风得意的金莲,渐渐郁郁不得志。如果她能随遇而安,像玉楼一样好心态,也能无事,但骄傲的金莲缺乏弹性。压力过大、压抑过久,便使她绝望、歇斯底里,甚至丧心病狂。这时的金莲是凶恶、丑陋并且残暴的。
第六十回官哥儿死后,金莲天天大骂瓶儿。“每日抖擞精神,向隔壁骂道:‘贼淫妇!我只说你日头常响午,却怎的今日也有错了的时节?你斑鸠跌了蛋——也嘴答谷了。春凳折了靠背儿——没的椅了。王婆子卖了磨——推不的了。老鸨子死了粉头——没指望了。却怎的也和我一般!’李瓶儿这边屋里分明听见,不敢声言,背地里只是掉泪。着了这暗气暗恼,又加之烦恼忧戚,渐渐精神恍乱,梦魂颠倒,每日茶饭都减少了……这李瓶儿一者思念孩儿,二者着了重气,把旧病又发起来,照旧下边经水淋漓不止。西门庆请任医官来看,讨将药来吃下去,如水浇石一般,越吃越旺。那消半月之间,渐渐容颜顿减,肌肤消瘦,而精彩丰标无复昔时之态矣。”可以说,瓶儿的死很大程度上是金莲促成的。这时的金莲,确实十分可恶。
瓶儿死后,金莲试图打起精神,重振旗鼓。然而,此时她因身负逼死蕙莲儿、害死瓶儿母子等许多恶名,性情更加暴躁。而月娘有了身孕,被西门庆敬让着,逐渐露出锋芒。终于,第七十五回,玉楼生日过后,月娘与金莲的妻妾大战爆发了。月娘控诉了金莲一系列罪行:控制西门庆;未经同意,私自取了瓶儿的皮袄;放纵丫头春梅,等等。双方实力太过悬殊,金莲很快败下阵来,最后不得不给月娘磕头谢罪:“娘是个天,俺每是个地。娘容了俺每,俺每骨秃叉着心里。”
对于金莲的境况,西门庆心里一清二楚。但就算他再宠爱金莲,也不可能乱了家庭的伦常,何况月娘有孕在身。第七十六回,面对金莲的哭诉,他只能“搂抱着劝”:“罢么,我的儿,我连日心中有事,你两家各省一句儿就罢了。你教我说谁的是?昨日要来看你,他说我来与你赔不是,不放我来。我往李娇儿房里睡了一夜。虽然我和人睡,一片心只想着你。”这大概是这个男人现在能做到的、对金莲的最大呵护了。
总的看来,西门庆对金莲感情的真挚程度毋庸置疑。这大概是金莲凄惶的一生中最值得欣慰的地方了。第七十九回,西门庆临死,最担心的不是孩儿,也不是月娘,更不是万贯家财,而独把金莲放在头一项:“见月娘不在跟前,一手拉着潘金莲,心中舍他不的,满眼落泪,说道:‘我的冤家,我死后,你姐妹们好好守着我的灵,休要失散了。’那金莲亦悲不自胜,说道:‘我的哥哥,只怕人不肯容我。'西门庆道:'等他来,等我和他说。’不一时,吴月娘进来,见他二人哭的眼红红的,便道:‘我的哥哥,你有甚话,对奴说几句儿,也是我和你做夫妻一场。’西门庆听了,不觉哽咽哭不出声来,说道:‘我觉自家好生不济,有两句遗言和你说:我死后,你若生下一男半女,你姊妹好好待着,一处居住,休要失散了,惹人家笑话。’指着金莲说:‘六儿从前的事,你耽待他罢。’说毕,那月娘不觉桃花脸上滚下珍珠来,放声大哭,悲恸不止。”西门庆不放心金莲的地方很多,比如她任性放荡、直言快语、有口无心,比如她好逞强、咬群出尖儿,比如她与现实脱节、不识时务,等等。由此可见,西门庆对金莲不仅十分了解,心中也确实对她有着深厚的感情。正是这份感情使月娘悲恸不止——这场妻妾大战,最终仍被西门庆宣判月娘失败,并且永不能获胜。西门庆虽然始终尽力掩饰这一点,但临死的仓促,令他无法再周旋下去了。
然而,西门庆既死,不管是由于钱财,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月娘都不可能再收留刺头金莲。但西门庆有遗嘱在先,这使月娘不得不费一番心思。这时,月娘很早以前给金莲设下的陷阱——陈敬济,便发挥了作用。金莲由于自己的性格缺陷,在西门府人缘欠佳,又与月娘不和,现在失去西门庆这个依恃,当时就有些慌不择路,急于寻找依靠。她亲见西门庆把家交给女婿敬济,后者成了西门府的第二代当家人,自然就选择了他。加上金莲大胆不羁,与敬济又有旧,所以行动起来轻车熟路。但是,金莲太过放纵贪欢,不能自拔,反而陷身绝境。月娘只是作壁上观,直等到时机成熟,才出来从容地一个一个打发掉,终于在不违背西门庆遗嘱的前提下,达成了心愿。
金莲被扫地出门,经历了如此大的变故与磨难,却不仅没有反思、成长,反而破罐破摔,愈加放浪形骸。金莲的放浪源于自负,而这自负又源于男人对她的簇拥与追逐——在她待价而沽时,先后便有陈敬济、张二官、周守备、何官儿等人慕名前来。然而,也正因为这种自负,金莲不假思索地走进了武松的屠宰场。
第八十七回,武松回来了。金莲正站在帘下,见他来,连忙闪入里间,还有些防备。然而,一听到武松说要娶她,金莲便等不及王婆叫唤,自己出去了。她向武松道了万福,道:“既是叔叔还要奴家去看管迎儿,招女婿成家,可知好哩。”如此大胆轻信,既是因为她的轻浮自负,也是因为武松对她的巨大诱惑。金莲甚至忘记自己曾杀了武大,更不去想武松完全可能是来复仇的。金莲走到屋里,浓浓点了一盅瓜仁泡茶出来,双手递与武松。
不能说金莲对武松的感情不真挚。比起嫁入豪门,金莲似乎更向往一夫一妻、当家做主、一家一计、恩恩爱爱的日子。不管是在青石巷,在西门府,还是现在,金莲一直都如此。所以当武松说到“一家一计过日子”,金莲便被打动了。这个刚从西门府出来、厌恶了“一个碗内两张匙,不是烫着就是抹着”的妇人,顿时感到了幸福。然而,金莲永远不能接受但又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是,她与所有男人的相遇,似乎都是孽缘。
如果最后武松能有一念之仁,放下屠刀,也善莫大焉。可是被仇恨完全占据的武松不可能有这胸襟,只有与金莲一样的偏执。他一刀戳在金莲心窝上,把头割下来。更用双手去斡开她胸脯,扎乞的一声,把心肝五脏生扯下来……如此血腥,如此暴力,如此泯灭人性,在这里,打虎英雄跟魔鬼一般无二。其实,武松对金莲、对复仇的偏执,与金莲对瓶儿、对母亲、对生活的偏执,也一般无二。这种可怕的相似,其中的前因后果,似有若无,令人深思。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感谢阅读
发布于 2025-05-05 05:22微信分享
扫描二维码分享到微信或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