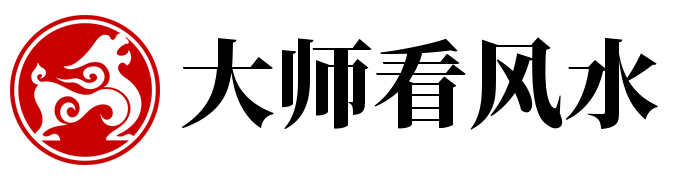那年头印尼撩妹“如歌的行板”|一位华商娶两个老婆的恋爱故事
01
本文开始之前,先讲一段我在印尼的往事。
2006年,我带着两个作家出国到了雅加达,住在当地一位女社会活动家的会所,打算与她合作当一个传记写作的“包工头”。
具体设想是:让那位颇有交际能力的女华人做老板,负责从华商大佬圈里拿“订单”,由我担任编辑当个二老板,再把写作的活儿包给国内来的专业作家,弄个选题采编一条龙,希望提高一下图书出版的效率。
那位合伙人女士很快确定了三个写作对象,都是印尼知名工商人物—— 一位煤老板H先生,一位金融业大佬L先生,还有一位是从事唱片影像光盘生产销售的女强人展姐。
我和两位作家老师分了工:安徽来的男老裴负责写煤老板H先生,河北来的女小娥被金融大佬L先生指定做了执笔人。另外那位年迈的女强人展姐的传记,则由我亲自操刀。
2006年5月,我和两位国内的作家朋友前往印尼时途经香港留影。
男老裴采访似乎很顺利,每天刷刷刷写得挺快,不到一个月就交了稿,领了稿费准备回国。
女小娥采写遇到了困难。原因有二:一是她生平最不感兴趣的就是有关财政金融的话题,所以完全听不懂那位传记客户L先生津津乐道的股市汇率,还有对冲基金等等枯燥深奥的专业术语——可是人家L先生身为金融界大咖,不谈这些谈什么呢?
我看女小娥愁眉不展,就劝她说:小娥姐,你们女作家,都擅长写点生活故事,或者多问问L先生的老婆孩子,写写他的情感经历,说不定也有些可读性。
女小娥把嘴一撇,更犯难了:“兄弟你也知道,这个L先生年岁不大,竟然公开娶了两个老婆。都什么年代了,还整这么一出!我一想就来气,你说我还写得下去吗!”
其实就印尼华商而言,从过去到现在,此类事情并不少见
最终一个月过去,女小娥勉强写了两三万字,把草稿给我,支了三分之二稿费就跟男老裴回国了。
因为当时传主并没有预付稿费,请作家来印尼,包括稿酬等费用,都是我个人垫付的。
事已至此,我只好一个人留下来独自凌乱。
H老板和L老板两位传主,读罢男老裴和女小娥的书稿,果然各自都不满意,认为文字虽然顺畅,但许多情节并非写实,而是凭作家的想象虚构的,因此必须认真修改。
我这才明白,国内专业作家尽管不乏写作基本功,但是他们来印尼之前对该国的一切完全陌生,要想让他们在短短一个月内,了解把握这个国家的历史背景和华人族群的方方面面,并且写成一本书,确实是勉为其难。
看来,不能怪两位作家朋友不努力,而是我那时的设想太乐观,以至于自己初出茅庐刚刚出版了两本书,就雄心勃勃企图当个“写作包工头”。结果步子迈得太大,一不小心,就扯着那个什么了……
没奈何!我不得不打起精神,赶紧补充采访,对书稿大修大改或干脆重写,费了很大劲儿总算完成任务,把亏空的费用找补回来。
后来,我也不再与人合伙,自己一个人在印尼采访写作,奔波往返,踏踏实实“单打独斗”,十五年过去,先后又写了十几部传记,业精于勤,越来越熟练,慢慢在这个行当摸出了门道。
如今回首往事,正可谓:惶恐过后说惶恐,南洋浮沉雨打萍。青灯孤影漂如梦,壮岁已逝白头翁。
再说那位金融大老板L老板,后来我接替女小娥写完了他的传记,补充采访时也多次接触了L府的两位夫人,了解到这个家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便在书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讲述他们的情感经历。
下面,我就把这一章节选一部分在本号发表。
我写的肯定是事实。当然,既然是树碑立传,就不可避免适当美化了一些情节。另外根据当事人的要求,我采用化名称呼他们,也不发布L老板和两位太太的照片,想必读者能够理解。
02
即使一个人在外面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如果没有家庭给他支持、休息和温暖,那么,他的成功也仅仅是霎那间的喜悦。——作者题记
如果把成功的人生比做一部交响乐,辉煌的事业固然是金戈铁马的华彩乐章,但情感和家庭却是温婉柔美、不可或缺的如歌的行板。
现在,让我们轻松片刻,从艰涩难懂的金融期货市场走出来,回溯一下本书主人公人生乐曲中的那段“如歌的行板”。
在L生的家乡S市——东南方向大约80公里,有一个地方名叫巴东实林泮(PADANGSIDIMPUAN)。这是北苏门答腊省的另外一座小城市,面积和人口都与S市差不多,它的中文名字又译作“帕当西登普安”,——从音节上讲,这样翻译似乎更符合PADANGSIDIMPUAN的印尼文名称,但当地华人还是习惯用口语化的中文称之为巴东实林泮。
印尼北苏省小城巴东实林泮,街旁几座马来风格的建筑。
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过,L生1岁到7岁的童年时代,是在实林泮的外婆家里度过的,他对这里的感情很深。因此,当他长大之后,始终把这座城市看作是自己的第二个故乡。
他外婆一家,早先住在靠近多峇湖的北苏省第二大城市先达(Pematang Siantar),后来搬到了巴东实林泮。而L生的母亲,就在这里度过了结婚之前的少女时代。
外婆家附近有一户姓Z的人家,这Z家的女主人是外婆的朋友,因此两家关系很好。
Z家早年来自广东南海县,育有8个子女,最小的女儿名叫Z仙,家人邻居都她阿仙。她曾经见过儿时的L生:“那时他还是一个小男孩,头发黑黑的,有一点卷,圆圆的脸,身上瘦瘦的,不过我们当时只是认识而已啦!没有更多的接触过。但是我知道他外婆是妈妈的朋友。”
这是阿仙小时候对L生的最早的印象和记忆。
接下来,让我们介绍一下巴东实林泮值得一说的人和事,这里不仅是阿仙的家乡,也是L生和她爱情生活的发源地。
说起这个实林泮,城市不大,华人却不少,有数万人之多,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华侨名叫梁四,在当地华人中无人不晓。
梁四祖籍广东开平,读了两年家塾,1910年由家乡出国来印尼苏门答腊岛。他先是在S市落脚谋生,并于10年后在S市创办了广胜隆建筑公司,承建该市自来水工程,及天主教堂与学校、庶民银行、邮政局、政府公署、华人和印尼人店铺等。又过了10年,梁四转赴巴东实林泮市开设建筑分公司,又先后承建了这里的电影戏院、基督教堂、市立医院、市立高中、市立初中学校、中心市场及民间房屋等一大批工程。
1949年荷兰军队发动第二次“警卫行动”,在攻占巴东实林泮市之前,印尼革命军发动全市实施焦土抗战,大举焚毁所有政府公署及重要设施。1950年,荷兰军队撤退,该市由印尼军政当局接管。恢复政权初时,军政当局委托梁四协助城建复原工作,重新兴建了新的市场、政府公署及其他重要设施,使之早日恢复繁荣。梁四全力以赴,不遗余力,致力于地方建设。不论是在城镇,或是在穷乡僻壤,他都竭心尽力,精益求精。他一生接触的华人印尼人,人数众多,不论男女老少,他都待人和蔼可亲。日子久了,大家融洽相处,梁四的名字妇孺皆知。
梁四先生生活俭朴,诚实待人,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积劳成疾,于1956年5月因病逝世,终年65岁。梁四生前交友广阔,出殡之日,前来送葬的近万名印尼友人和各地侨胞排列一公里多,最终安葬于实林泮中华义山坟场。
2006年3月,实林泮市政府暨议会为表彰对地方建设具有卓越贡献的已故华人梁四,将该市JL·DANAU LAUT TAWAR 大街正式命名为梁公街 (JL·LIONG SEE),这不仅是当地华人的骄傲,也应当是印尼华族的光荣。
本地大名鼎鼎的华人老前辈梁四先生去世的时候,Z家小妹阿仙才只有四五岁,自然不曾记得上述事情,当她稍大一点之后,就听说过这个名字,并对其充满敬仰。
提起家乡的名人梁四,Z仙姐兴致勃勃地告诉笔者。
“梁四先生的墓地很大,建在一个山坡上,有很高很高的台阶,我小时候还去上面看过。后来,梁四的长子梁舜炽先生也来到椰城发展。我们在雅加达成立了巴东实林泮旅椰同乡会,大家就推选梁舜炽先生担任了同乡会的副主席。”
1958年,L生该上学读书了,就从外婆家回到父母所在的S市读小学去了。第二年,阿仙也在本地开始念书。她先是就读于一所右派华人办的“蓝色”小学,1960年,“蓝色”华校因故被政府关闭,她和大部分华人孩子又都转到左派办的“红色”华校。1966年读到初中毕业,所有华校都被政府强制接管了,阿仙也和在S市的L生一样,无缘再上高中了。
走出校门,青春如诗的岁月随之来临,1970年的阿仙,已经出落成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她长着一张秀气的瓜子脸,眼睛里常常闪烁着羞涩但却明亮的光芒。
这一天,阿仙正在和几个朋友在一起玩,一个长得很精神的圆脸庞青年,微笑着加入了他们的圈子。哦!——原来是儿时认识的那个寄住在外婆家的L生,他现在也变成了一个英俊帅气的小伙子了。
Z仙和伙伴们都还记得L生,年轻人热情单纯,大家围着他问长问短,说说笑笑,马上又都熟悉起来。
令本地这伙年轻人非常羡慕的是,L生有一辆大马力的日本雅马哈摩托车,而且他是从S市一路骑过来的。30多年前的实林泮还是一个简朴的小城,那时候人们出门如果去不太远的地方,一般都步行或者骑脚踏车。眼前的L生,穿着紧身茄克衫,戴一顶红色头盔,跨着那辆威风凛凛的雅马哈,来去都是“突突”轰鸣着一溜烟就到,又英武又潇洒。
在这群男女朋友中,L生看上了文静腼腆的阿仙,开始处心积虑地想办法接近这个女孩子。可是他平时住在S市,而Z仙却在实林泮,彼此相距80公里,怎么才能经常见面呢?多亏L生有辆雅马哈,自从喜欢上Z仙之后,他便采取了一种锲而不舍的方式紧追不放——每个星期都骑着摩托车来找她。具体说来就是,一到星期天,L生不必在家里的店铺上班了,——清晨天刚亮,他就出门骑上雅马哈冲出S市市区,沿着盘山公路狂奔两三个小时,到实林泮刚好九、十点钟,接着马上就去Z仙家里约她出来,或上街随意闲逛,或去郊外游玩,总之,只要和阿仙在一起,他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愉快。
玩了一天,夜晚到了,L生就依依不舍地送阿仙回家。星期一又要在父母的杂货店做工了,他大清早再骑着摩托车赶回S市。
然后,又盼着下一个星期天的到来。
每当L生前来约会阿仙,两个年轻人最爱去的地方是实林泮的电影院,那时候印度电影正在印尼大行其道,L生和Z仙便结伴看了大量优美活泼的印度爱情片。
典型的印度爱情片里,主人公无一不是俊男靓女,载歌载舞,又蹦又跳,剧情简单而又公式化,但却拍得热闹有趣,生动感人。尤其是节奏鲜明、婉转美妙的电影插曲,更令人一曲难忘,非常符合同样能歌善舞的印尼观众的胃口。
除了看电影之外,他们也常去品尝街头的印尼小吃。
“呵呵!我家L生那时候最爱吃的就是小摊上的沙嗲!”Z仙笑盈盈地回忆说。
这沙嗲,乃是印尼最具民间性的小吃之一,在印尼各地城乡的巴刹(市场)和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有叫卖沙嗲的摊贩。人们经常可以在那里看到一群人围住沙嗲摊档,边看摊主烤着香气四溢的鸡肉串(或牛肉、羊肉串),边谈笑风生、十分过瘾地吃着这种风味小吃。看起来,“沙嗲”似乎很像中国新疆的烤羊肉串,区别在于调味的佐料,“沙嗲”本是一种辛辣香甜的复合味调料酱,而中国新疆的羊肉串则是用香味浓烈、样子和辣椒面差不多的“安息茴香” ——“孜然”(维吾尔语)洒在上面一起烤。
印尼的烤肉串离不开沙嗲酱,沙嗲酱的做法也颇讲究:先将花生米炒熟捣碎,再用火把虾糕焙香;然后将大茴香、丁香、芫荽子、胡椒、红辣椒干、香茅、黄姜、南姜、小红葱、蒜瓣,分别用石臼捣成粉末或泥状。最后用花生油热锅,先倒入红辣椒末,徐徐加热成红辣椒油,将葱、蒜下锅爆香,再加虾糕炒至香味四溢,然后将其他调料投入锅中同炒,用中火一边炒一边加油,最后加花生碎末、椰浆及盐、糖,调制成香味浓郁略带甜、辣的沙嗲酱。印尼人坚信只有蘸着沙嗲酱吃,烤肉串才成为美味佳肴,因此该国和马来西亚等国老百姓便将烤肉串也称为“沙嗲”。
每当傍晚,暮色升起,便有无数收了工的印尼人随手买几串沙嗲,边走边吃,兴趣盎然;在树林草坪之间,更有不少青年男女四目相对,含情脉脉地吃着从对方手中伸过来的沙嗲,多少年来,如此浪漫的情景,早已在千岛之国城市乡村构成了一幅经典动人的风俗画。
同样的风俗画里,L生和阿仙的爱情也在慢慢滋长。不过,七十年代年代初的印尼小城镇,华人男女在恋爱方面还比较保守。阿仙记得,她与L生交往已经很长时间了,坐他的摩托车兜风时,自己还是不敢抱住他的腰。
有一次他带我去S市玩,领我参观风景区,还用照相机为我拍了不少照片。后来我坐在他的摩托车后面,又不敢搂着他。结果他猛一加速,摩托车向前一窜,一下子把我摔下来了,他还不知道,继续往前开。直到我大叫起来,他才回头,看到我穿的裤子的膝盖都碰破了,他就很抱歉,说是要赔给我一条新裤子,但是最终也没赔。不过呢,从那以后我再坐他的摩托车,很怕又摔下来,就顾不上害羞,不得不抱住他的腰了。
网络图像,非文中主人公。
事实上,在L生爱上阿仙之前,阿仙的身边也不乏追求者。实林泮本地就有一个华人小伙子,早在上初中时便暗暗喜欢阿仙。那小伙儿骑着一辆脚踏车,每天放学回家都故意骑得慢慢的,跟在步行的阿仙旁边。虽然没有很明确地表白,但心思敏感的少女不会不知道那位男同学的意思。朦朦胧胧的,阿仙似乎也不讨厌那个人。后来,“摩托骑士”L生的出现,姑娘感情的天平便迅速倾斜到他这一边。
Z仙对笔者说:“其实,我那时候人很单纯的,喜欢一个人,很少考虑到物质方面的因素,所以并不象你们开玩笑说的那样——见了骑摩托车的就不喜欢踩脚踏车的了。我认可L生,除了他这个人朝气蓬勃,喜欢看书,比较有魅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的父母家人都很看重他,因为他外婆是我妈妈的朋友,而他母亲也是我妈妈看着长大的,老一辈人知根知底,认为我应该嫁给L生。”
为了追到自己热爱的姑娘,L生每周一次,骑着摩托车往返于S市和实林泮之间,其雷打不动的执着精神和韧劲儿,也令阿仙大为感动:
他大清早骑着摩托车从S市来看我,山路上的风是很硬的,为了让自己暖和一点,他每次就拿一摞报纸挡在胸前,外面再套上一件茄克衫。还有一次我有事去棉兰亲戚家里了,当时没有电话没法提前告诉他。那天他从S市赶来没找到我,他马上又搭乘长途汽车连续跑了七八个小时,一直找到棉兰我亲戚家,见到我了才罢休。哎呀,我当时真是又感动又心疼!更加死心塌地要跟他好了。
尽管如此,当1973年10月L生离家出走,只身闯荡雅加达时,为了不动摇自己的决心,他以极大的毅力暂时克制了对心上人的感情,没有告诉阿仙。
在L生志在天涯的梦想中,男子汉大丈夫必须以事业为重,出门在外没混出个名堂之前,决不能因为儿女情长而英雄气短,如不立业,安能成家!
他当然不会忘记自己的女友。半年之后在雅加达站住脚了,L生开始写信给阿仙,直到第二年春节,他回苏北过年,一对恋人在家乡才重又相聚。
1977年,L生在外闯荡三年,事业有成。这一年他26岁了,爱情长跑终于到达终点。这一年的农历正月初十,L生意气风发,衣锦还乡,在S市一座中国式的教堂里大宴宾客,伴随着亲朋好友的祝福,热闹隆重地迎娶了25岁的新娘阿仙……
03
看到这里,读者可能会问:既然L生和阿仙郎才女貌,有情人终成眷属,那他怎么又娶了第二房太太呢?
原来,1980代L生在雅加达开始涉足金融市场,玩期货交易,做汇率平台,没过几年就发了大财。这期间,太太阿仙连续为他生了一儿两女三个孩子。老公有钱,全家人很快住进了豪宅大院,锦衣玉食,香车宝马,样样不缺。
可是阿仙个传统型的女人,一切以丈夫为中心,性格内向,不善应酬,总爱待在家里,喜欢亲自煮饭、做菜、操持家务,每时每刻把房间内外,中堂庭院,打理的窗明几净,一尘不染。
L生在公司请了一位女秘书,同样姓L,祖籍福建,也在苏岛长大,生得鲜眉大眼,高大丰满,称得上英姿飒爽。L小姐性格开朗,非常能干,三下五除二,就帮老板把公司里里外外,大事小事,整得清清楚楚。
L生有了L小姐,简直如虎添翼,事业蒸蒸日上,自然对其青眼有加。
而这位L小姐比L生小六七岁,当时也才20多岁,尚未婚配。眼见得自己的老板年轻多金,帅气阳刚又胆识过人,接触久了,难免忍不住芳心暗许,恨不相逢未娶时。
中国有句老话:男追女隔重山,女追男隔层纱。为什么?因为不论在身体或生理方面,都是男强女弱。一般上,强者去追求弱者,弱者本能地就会防守,理由是:他为什么会追我呢?他是不是就是为了播散种子呢?如果有了种子,他不管,我又该怎么办?——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就会在女人脑海里浮现。
反过来,女人追男人,就是弱者追求强者,男人骨子里会觉得女人不会对自己造成攻击性和危害性,这个攻击性和危害性主要是指有了那个关系之后带来的伤害,男人会觉得不吃亏,所以基本抵挡不住对方的追求。
当这种强弱关系演变成财富和个人能力,也就成为社会的生存价值。
如果把以上论述换成一句直观的话:那就是播种的人,找拥有土地的人合作比较难;而拥有土地的人找播种的人合作就相对容易的多了,因为土地是稀缺资源。
总之,老板L生和秘书L小姐,生意场上相得益彰,私下里也是日久生情。说不清是哪一天,面对聪明能干的L小姐,L生一下没把持住,就“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然后便是头发不剪越长越长。虽然L生已有老婆孩子,但两个人的感情到这一步了,谁都难以割舍,当然L生也无法放弃贤良温顺的阿仙和三个可爱的孩子,而L小姐宁愿L生不离婚,也要跟他在一起。
在L生的围城内外,一方是与自己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这个人,另一方又是工作中配合默契、耳鬓厮磨的那个人。患难结发夫妻和铁杆红颜知己,孰轻孰重?情理和法理的巨大冲突,确实是非难辩!
很多时候,即使让最擅长表达的人也难解说。
那段时间,和所有丈夫有了新欢第三者的妻子一样,软弱的阿仙也像疯了似的,跑去公司哭叫打闹,寻死觅活,甚至苦苦哀求,要L小姐不要抢走自己的老公。而L小姐却铁了心,平静坚定地告诉阿仙,我并不想抢走L生,只是想和你共同拥有他。请不要怨恨我,是上帝让我这样做的,我拒绝不了。
闹到最后,L生终于不顾各种压力,坚持把L小姐娶过来,成了他的二夫人。好在他有的是钱,又在另外地方买了一座豪宅,妥善安置了L小姐。
从此,L生在雅加达有了两个家,大太住在东边,二太住在西边,两家相距七八公里。这位二夫人也接连给L老板生了三个孩子,事已至此,大太阿仙没办法,只好默认了二太的存在。
L生摆平了风波,每个星期轮流回到两边的府上,享受着齐人之福。他有时难免得意,便把大太和二太的住家分别称为“东宫”、“西宫”。
我为L老板写传记写到这一章时,他向我提了个小小的请求:
“丁先生,你能不能用妙笔生花的文学语言,正面表述一下我有两个老婆这件事,就算不合时宜,也让读者感觉到美好的一面。你也看到了,我喜欢小夫人,但是对大太太阿仙还是很好,我不是那种没有良心的人。”
我琢磨了半天,用了下面这段话,满足了这位传主的愿望:
爱着,便有按捺不住的热情向往,便有牵扯情怀的无限眷恋。便如白帆张开,凌波踏浪而去;便如满月悬空,清辉盈宇而来。
爱着,超越了痛苦,使痛苦美丽;穿越了忧伤,使忧伤美丽。但是它也使仇恨更深刻,使愤怒更急迫……
话虽这样说,但毫无疑问,这位拥有“东宫、西宫”的L老板,虽然比一般人享受了更多的爱,也肯定比一般人付出了更多沉重的心力和代价。
至于是什么代价?以后有机会我再写出来吧。
发布于 2025-07-29 01:26微信分享
扫描二维码分享到微信或朋友圈